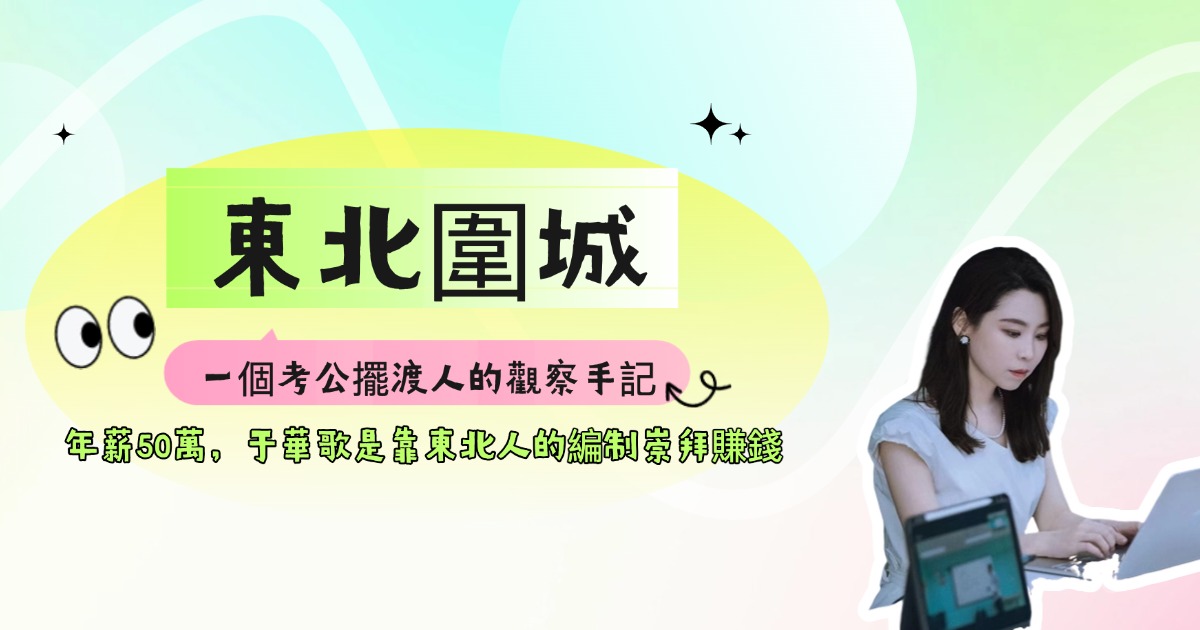
于華歌結束一天的教學任務時,已經凌晨 12 時多了。作為某頭部考公教育機構長春培訓中心的申論老師,這已是她連續第九年與學生一起從早上 8 時到深夜高強度 「備戰」。走出培訓酒店,手機螢幕上跳出一條消息:「老師,我進面(面試)了!」她疲憊的臉上浮起笑意,隨即又歎息一聲 —— 在中國東北,編制就是信仰。
記者:白露

這並不誇張。吉林大學(東北影響力最大的綜合類大學之一)發佈的《吉林大學畢業生就業品質年度報告(2023屆)》中指出,該校2023年有26.55%本碩博畢業生進入國企,居於就業單位第一位,而本科畢業生進入國企的比例更是高達43.7%,兩項數據均超全國平均水準。由於東北三省(遼寧、吉林和黑龍江)經濟多年來無新的增長點,青年人能選擇的崗位很少。據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,東北十年間流失超過1100萬人。「想闖的只能背井離鄉,而留下的,就得有個編(編制)。散盡千金換一個確定性。」于華歌說。
在中國大陸,公務員和編制人員均屬體制內正式編制,受法規管理,從事公共服務且職業穩定。公務員屬行政編制,行使國家行政權力,服務於行政管理部門;事業編制主要在事業單位提供教育、醫療等公益服務或專業技術支持等。兩者都需要考試,公務員考試(考公)由政府組織,編制考試(考編)由事業單位組織。

體制即尊嚴:思維模式的代際傳遞
于華歌的一個學生叫陳琪,今年23歲,這位應屆生的考公選擇折射著東北青年的困境。陳琪父母在吉林縣城體制內工作半生,早已將「吃皇糧」視作人生最穩妥的選擇。「他們覺得公務員是當官的,走到哪兒都有面子,即使賺不到多少錢也能被人高看一眼。」這種觀念在陳琪身上形成雙重枷鎖:既背負著家庭期待,又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「體制即尊嚴」的固化思維。
陳琪並非沒有嘗試突圍。大學期間她曾在上海實習,但快節奏生活帶來的衝擊遠超預期:「月薪三分之一交給房東,加班到地鐵停運是常態,看著同事們的體檢報告,覺得一個女孩子這麼賺錢把身體搞壞了不值得。」當被問及為何不選擇家鄉私企時,陳琪無奈地說:「東北的機會實在太少了,冬天太冷企業不願來,經濟也不活躍,投資不過山海關這句話人人都知道」。陳琪又低聲補充,「公務員無論考試還是工作內容,要求都不是很高,它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,在固定的框架裡按照別人的思維方式去考慮問題就可以了,很適合我這種沒什麼想法的人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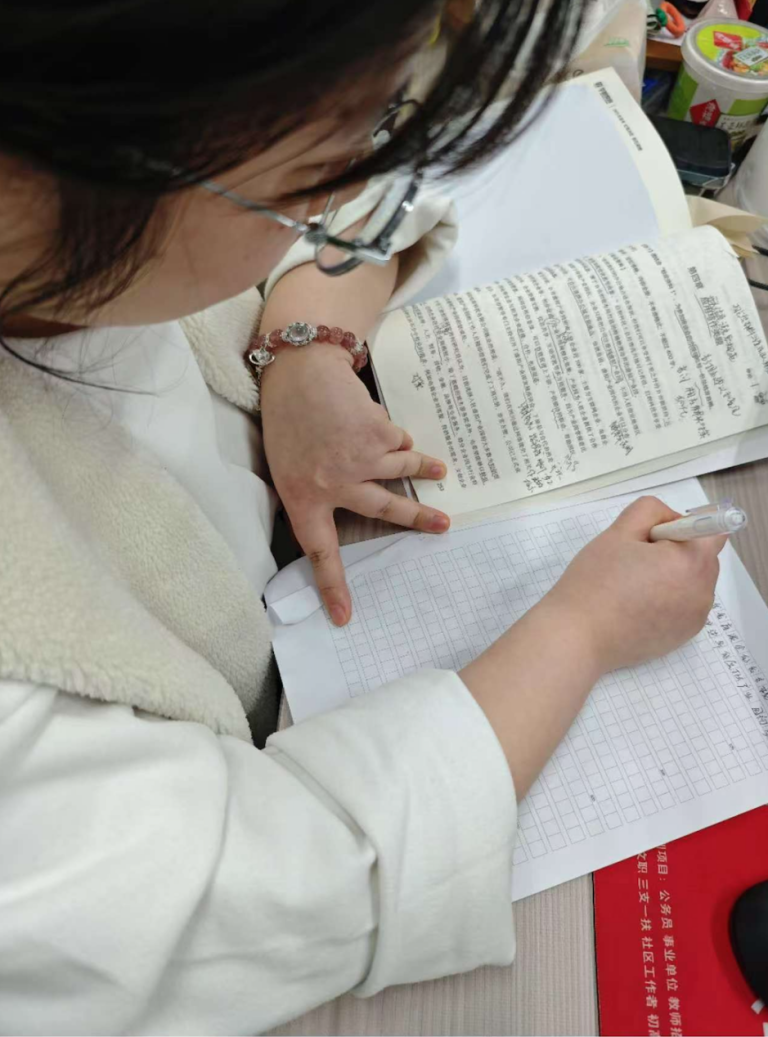
「不需要創新突破,按既定流程辦事」,陳琪的低風險生存模式,恰與東北「穩定壓倒一切」的集體潛意識相契合,這種集體認知源於東北特有的歷史背景。被稱作「共和國長子」的東北,製造業曾經佔據全國的半壁江山,形成了獨特的大集體模式。直到2015年,遼寧省鞍山市區的145萬人口中,鞍鋼集團的覆蓋人口就達到65萬。而長春的中國一汽集團鼎盛時期,約30萬員工及其家屬構成封閉的「單位社會」。
27 歲的張明(化名)是于華歌筆試班學生,他就是成長於這樣的廠區子弟家庭。長春大學畢業後回到家鄉,他拒絕所有企業錄取,一心撲在考編上,連續四年參加國考、省考和事業單位招錄考試,屢敗屢戰。對他來說尤其難的是考公務員,有些崗位需連闖筆試(行測和申論)、面試、體測、政審、公示五關,淘汰率逐級攀升。他最後一次就卡在面試上。「父母一直資助我,他們說只要能考上,花多少錢都願意。」 但看著同學們都漸漸有了工作,張明陷入焦慮,甚至患上抑鬱症。第四年省考放榜,他再次落榜。那天,他在考場外蹲了許久,突然意識到:「或許我該換個活法,公務員根本不是我想要的,那是我父母想要的」,張明說。
從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,東北製造業國企下崗人數達400多萬,這個數字佔全國製造業國企下崗數的17%。張明的母親53歲,也是下崗潮中的一員。她告訴記者,那時候在國企吃的是大鍋飯,孩子們上的是廠裡子弟學校,就連生病了廠裡也有診所,有的單位效益好還會分房子,誰到年紀退休了崗位直接給自家親戚上,「大家都以為能這麼幹一輩子。」
直到國企改制,集體買斷工齡自謀出路,她開始失去營生,一夜之間所有的福利都被取消,幾萬塊錢的買斷費兩、三年就花完。「那幾年上有老下有小,為了吃口飯,在雪地裡開過三輪車、在飯店當過服務員、還在光復路路邊擺攤賣過內衣襪子……什麼苦都吃過」。現在即使家庭條件仍不是很好,她也要湊錢供兒子備考,因為她不希望兒女重蹈自己覆轍,同時也懷念著那些在國企旱澇保收的日子,「進入體制內工作多大歲數都不會被裁員,空閒時間多,日常補助津貼年終獎都多,這些都是私企比不了的,就算我兒子考不進去,我也得讓他娶個公務員」。
集體買斷工齡是指改革開放初期,一些國有企業在改革過程中安置剩餘人員的一種辦法,即經企業與員工雙方協商,由企業一次性支付員工一筆金額,從而解除企業和剩餘員工之間的勞動關係。
從獄警到考公名師:無法跳出的體制圍牆
其實于華歌自己的經歷也和這些東北年輕人相似。因為家裡三代從警,自幼,父母就為她規劃好了成為公務員的道路。大學期間,她全身心投入備考,成功上岸成為獄警。然而,這份工作帶給她的更多是內心的煎熬。看到犯人因手續延誤就醫,她在同情與鐵面間難以釋然。「喝茶看報是外界對體制內的刻板印象,實際上基層工作很累,不僅工作累心裡更累,但為了穩定,東北人還是擠破頭想進來。」2015 年,于華歌不顧家人反對和外界質疑辭去公職,同事們戲稱她是「監獄系統辭職第一人」,「辭去年薪10多萬的體制內工作,家裡人對我很失望,差點斷絕關係」。
離開體制後,于華歌憑藉考公經驗和對培訓行業的瞭解,投身考公培訓領域。如今,她已成為高級講師,負責中高班學員和機構內部培訓,年薪升至 50 萬元人民幣,在長春這座平均工資只有4000 元人民幣左右的城市,堪稱天文數字。看似「職場贏家」,但于華歌實則認為自己仍在吃公務員這碗飯,「本質上我還是在利用東北人的編制崇拜賺錢,這是東北人跳不出的圍牆。」

經濟短板:催生「官本位」思想
東北地區對體制的信仰,本質是民營經濟結構性塌陷催生的生存策略。東北受計劃經濟影響最深,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沒有發揮決定性作用。當市場長期缺位,人們只能退回體制尋找確定性。
在《2022 中國民營 500 強榜單》上,東北三省僅七家民營企業上榜,剛到浙江省(107家)的零頭,也僅僅是山東省一省的14%。這種懸殊差距並非偶然,由北京大學聯合武漢大學發佈的《中國省份營商環境評價》報告為其做了注腳——黑吉遼三省營商環境分別為第21、20、22名,位於B和B-級,僅優於廣西和西藏。報告認為,中國各省營商環境的特徵為「七大區域差異顯著,華東地區明顯優於其他地區,東北和西北最為落後」。

遼寧大學校長余淼杰教授在《東北地區民營經濟發展問題探析》中解剖了這種畸變的經濟肌體:東北地區長久以來形成的「重國有、輕民營」使民營經濟占比過低;而對招商引資過程中承諾提供的稅收、土地和政策優惠落實不到位的現象時有出現,損害民營經濟合法權益和發展信心等,都使「官本位」思想根深蒂固。
創傷記憶:從下崗潮到編制信仰
經濟因素之外,還有集體創傷後的應激反應。著名媒體人、東北問題研究學者維舟告訴記者,「下崗潮帶來的衝擊,讓人們在缺乏制度化托底保障的情況下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,沒有安全感,而獲得安全感的現成方式就是進入體制內,有個穩定的飯碗,這種創傷讓人們格外看重穩定」。
維舟認為,東北原本就是計劃經濟色彩最濃厚的地方,又經歷了下崗潮,人們脫離體制後,在沒有保障的情況下面對一個充滿不確定風險的市場,比別處更能強烈感受到自己有多脆弱。也是因為這樣的歷史條件,東北還沒有像市場化順利轉型的地區那樣靠市場的「無形之手」調節,這種現象在其它地方很少,這又導致普通人要依靠自身力量來確保人身和資產安全,比其它地方更不容易。創傷在代際間傳遞,父母將下崗記憶轉化為對子女編制的執念,而年輕人則在東北經濟不斷萎縮的陰影下,將編制視為抵禦風險的堡壘。

于華歌最近喜歡一部電視劇,叫《漫長的季節》,其故事背景發生在東北國企改制時期。裡面的主角們都生在廠裡,長在廠裡,以廠為家。于華歌說:「你看二、三十年過去了,什麼都變了,又好像什麼都沒變,這是屬於東北人的漫長的季節。」
